|
|
感谢关注耳机俱乐部网站,注册后有更多权限。
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,没有账号?注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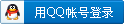
x
严锋:知音
熟悉父亲的人都知道,他这个人太好,但命运对他太不公,这辈子过得太苦,磨难冤屈之深重,没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难以想象。但是父亲说得也对,上苍另一方面待他也不薄,给了他音乐和书,还有李章这样的知音挚友,其道不孤,确是苦难人生中的难得的快乐。
1991年3月,我从南通去复旦报考贾植芳先生的博士研究生,见到陈思和老师,他说真巧,王安忆和李章去南通看望你父亲了。王安忆当时已名满天下,我也已经做她粉丝多年,但她的先生李章还是第一次听说。几天后回到家中,听父亲讲起他们夫妇的这次来访,我问他对王安忆有什么印象,他几乎说不上来,关于李章却说了很多,看来他的注意力全放在李章身上了。
这也难怪,父亲对当代文学相当隔膜,音乐才是他更熟悉的语言。他爱了音乐一辈子,却始终把自己定位为业余的门外汉,对门内的专业人士有特殊的敬佩。李章做过乐团指挥和作曲,属于父亲心目中的“专业人士”。后来又编辑大名鼎鼎的《音乐爱好者》杂志,在《读书》杂志上看到父亲的专栏,当即约他为《音乐爱好者》写稿。
对于一位名不见经传、身居外省二线城市南通的民间爱乐者来说,自然有知遇提携之恩。但是父亲对李章,有着超越共同爱好和编辑作者的关系。他常对我说,李章是个好人。在父亲的语汇中,好人是他对人的最高评价,非常难得。他自己也是好人,好人对好人,老实人对老实人,认真的人对认真的人,又有共同的爱好和话题,从此开启二十多年的友谊。
对于这第一次见面,李章这样写:“辛丰年焕然一身新军装,早早地等在我入住的有斐饭店门前,濠河在他身后流淌,这画面庄严郑重,令我肃然。”我是在父亲去世后看到李章的文章才知道这情景,父亲对物质看得极淡,收入又都投到书籍和音乐上,对衣服食品都完全不讲究。那套离休时发的新军装就是他最好的行头,极少的场合才穿上,他真的是对李章的来访看得很重了。二十二年后,李章去南通与他告别,也是一身黑色正装。李章说,这就像奏鸣曲式的两端,呈示与再现。
在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,我发现了不少李章的来信,都非常长,有的还精心地贴着各种照片。这些信都放在父亲写字桌的抽屉里,在他最触手可及的地方。这也令我吃惊,因为父亲这些年来经过两次令他痛苦不堪的搬家,已经把他的大多数个人物品都“处理掉”了。书和唱片都送给了我和他的朋友们,自己只留了约一百本,因为要和我弟弟、弟媳一起生活, 他不希望自己的东西占太多的空间。他就是这么个极端为别人考虑的人。
同样,李章也保留着父亲二十年间给他的几乎所有信件。在这些信里,他们谈稿子,谈怎么办好杂志,谈音乐,谈淘碟,也谈自己周围的事情。从这些信中能看出父亲很多文章的缘起和修订过程,看出他晚年爱乐的心路历程,也能看出世事风尚的变迁。这些年,无论音乐还是其他东西,都变得太快了,但是父亲和李章之间的相知相敬不变。
不变的还有父亲对李章的称呼:“李章同志”。今天的年轻人看到这称呼会觉得很奇怪,至少不相信这是老朋友间熟稔的语气。但我知道对父亲来说,“同志”就是他亲切而尊敬的用语,其意义超越世俗与时间。
不变的还有父亲这些书信的文笔,平实、简洁而有味,一如他的文章,只是更家常随意,读起来更放松。感谢李章的精心保存,我读这些信的时候,差不多能比较完整地还原父亲这几十年写读的历程。我所知的,可以参证;我不知的,可以补充。
父亲给李章的第一封信是1990年6月4日发出的。这一段时间,他们主要谈论的是《音乐爱好者》开专栏的事。据李章说,他给父亲的第一封约稿信是写给《读书》编辑部,让他们转发的,不久就收到回信。当时《读书》的君子之风,可见一斑。
有意思的是,父亲也谈了很多对杂志的设想和创意,从选题、栏目的设置,作者的推荐,到版式的改进,从一开始就提了许多建议。这种对杂志本身的关注,对上面文章的评点,一直延续了整整十年,直到李章离开《音乐爱好者》。我后来也参加办过杂志,今天重读这些信,换一个角度看,感觉他的编辑思想相当不俗。
推荐的作者,比如徐迟、方平、鲲西、程博垕、何满子等等,都非常对路。而且他好事做到底,往往连人家的地址电话都附在信中。父亲外表冷峻严肃,其实骨子里极热心,尤其是对他感兴趣的人和事。另一方面,父亲当过多年福州军区军报《解放前线》的副主编,对办刊业务是熟悉的。有时候我也会想:假如“文革”前也有《音乐爱好者》,假如我父亲不是编军报,而是编音乐杂志,会更加人尽其用吧。想到这里的时候,我就忍不住又要感激李章,是他激活了父亲心中早被埋葬的许多热情和梦想,让他后来的人生得以弥补许多缺憾!
这些信就像父亲的为人,完全没有废话,毫不矫饰。一切人事,喜欢的就是喜欢,不喜欢的就是不喜欢,直抒胸臆。正在看的书,正在听的音乐,他会热情地推荐(或不推荐):
这一期全阅过。赵晓生的文章我很欣赏。你们应该盯住他多写一些。可憾《钢琴之道》至今看不到!(1991)
《天下风云一报人》《费正清对华回忆录》都很值得一看,《红楼启示录》就绝妙!此公真是“学者化”了,了不起!(1991)
陈丹青文写得好,中国画人多能文,乐人似不如。(1993)
《燕乐探微》。才看了一部分,觉得既有见解,又有文采,很吸引人读下去。(1993)
不知注意到《布拉格》没有?我现在才发现,这是他最美妙的交响曲之一。尤其是第一章,那复调性与交响性真是太好听了!(1996)
前几天把莫扎特《布拉格》又听了一遍,享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欢悦,几乎是ecstasy(狂喜)的感觉!我有两张,一是拿索斯的,一是DG中价片,是伯姆指挥维也纳,后一张更精彩。前些时函购(广州)到比切姆指挥的戴留斯选集,Decca双片,这也是我最陶醉的音乐,前年无意中发现,中文中的“惆怅”一词,在英文中似乎找不到对应之词,为此还特意去买了一部《林语堂汉英词典》,仍无结果。现在又发现,戴留斯的音乐即是“惆怅”一词的好注解!不过真正中国味的“惆怅”还须到黄自的《玫瑰三愿》《春思》,以及陈田鹤的《江城子》中去找。(1996)
但父亲不仅是热心的推荐者,也是谦卑的学习者和聆听者。这些书信也可以看出父亲几十年求知的足迹。他是个特别不愿麻烦别人的人,但是一涉及想看的书和音乐,这些自律仿佛土崩瓦解。他不断请李章帮他找书,找碟。1994年,他终于咬牙买了个索尼的CD随身听,碟片也成为他俩重要的话题。父亲退休金微薄,无力负担太多昂贵的正版碟,连盗版碟也只能省着买,所以这方面信息的交换就格外重要。但是,若遇到真正心仪之物,他会毫不考虑价格的问题:“今昂贵若此,只好等等再说,但假如有莫扎特钢琴协奏曲全集,则愿以千元购之。不知有没有?拜托留心!”
信中提到的一个人名,特别让我感慨。1991年,我父亲应我中学班主任杨老师的邀请,义务为他们中学设计音乐欣赏课程,推荐曲目。父亲并随杨老师赴上海挑选唱片。在延安中路537号中图进出口上海分公司,父亲见到一位也是义务在那里帮忙的程博垕老师,两人相谈甚欢,并留下地址通信联系。这位程老师,是上海爱乐者中鼎鼎大名的人物,对唱片熟得不得了。父亲向他请教了许多问题。
我后来去中图也几次与程老师攀谈,受益匪浅。说到程老师,我就想起我最佩服的上海爱乐者兼音响制作者,一位自称“勃总”的网友。勃总身怀绝艺,睥睨天下,骂遍网络,真个是谁都不放在眼里。后来我专程去虬江路音响市场拜访勃总,他说音乐界他最佩服两个人,一位是程老师,另一位就是辛丰年。勃总的真名叫严峰。
父亲常赞李章的信内容丰富,很有看头。父亲这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几乎没有机会听现场音乐会(当然在“文革”前很多作品他连唱片也没有条件听到,只能通过读谱来感受),“文革”后,开始有世界顶级的乐团来访,但一则路途遥远,资费压力大,另一方面父亲也日渐年迈,无力远行,连吴祖强先生邀他去北京听世界四大乐团的演出也只能忍痛谢绝。
而李章这方面的活动很多,每听必向父亲详细描述现场情景,使他感同身受,过过干瘾。这些年父亲对音乐界的活动的了解,很多都是从李章那里来。父亲也会把自己的理解与李章的现场报告结合起来。比如李章听了圣彼得堡国立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后,他们对里姆斯基-科萨科夫的《西班牙随想曲》进行交流:
李:“可能我正受到您《兼听则明,冷暖自知》文稿的影响,跟同时演出的里姆斯基-科萨科夫一比,《西班牙》就是华丽,别的就没剩下什么了。而我以前是多要听《西班牙》呀!总谱也曾背过的,当时我特别迷里面的小提琴Solo。其实他们演奏得最‘原本’,一开始全奏就出我意料,主要是齐。齐,其实很不容易。还有铜管的和弦短促有力,刀切一般,又有弹性。短,其实也不容易,尤其发音迟滞的长号、圆号等,我们的乐队就是做不好。”
辛:“你说《西班牙》只有外在效果,我倒觉得它比《天方夜谭》耐听,有热力,有较真的意境,可能因为里姆斯基-科萨科夫对西班牙的乐与舞感受深于‘东方’的?‘伪西班牙’胜于‘伪东方’。此作之配器当然是很有听头的,可惜总谱上有的东西,唱片上听不见。例如弦乐的泛音,这次你听出没有?(如总谱[人音版]P.75)我笔记上有两条,可以奉告……”
这样隔空的音乐对话,还有不少。盛年风景,相知乐事,是任何文章中难以见到的。
信中经常可以看到父亲说自己这也不懂,那也不懂。这不是矫情,确实是他的真实想法。父亲是把自己看得很低的,有个出版社出了本集子,收录了文人谈乐的文章,中国的收了他和李皖及另外一人,其他都是萧伯纳、茨威格等外国作家,父亲就很生气,觉得不应该把他与那些文豪并列,中国部分应该选更好的代表。
李皖曾经在《读书》写过一篇论父亲的文章,对他颇有批评,大意是他那种风格过时了,不太适合现在的爱乐者。当时朋友们读到这篇文章后都十分生气。但父亲却说他批评得有道理,在给李章的信中对李皖相当赞誉,并建议把李皖批评他的文章收到将要出的集子中,让读者可以更好地选择。
父亲的另一遗憾,是他觉得难以走进西方现代音乐的门槛:“来信使我为之震动又茫然自失的是那句话:20世纪将逝,而我们对它的音乐知之甚少。我痛感到自己对现代音乐之无知,但要补救似已无及,很有可能我自身也将随20世纪而去。可能还等不及。即便19世纪18世纪的,我所知也不多。要争取补课的话,补哪一头?我真是两头不着实了!”
与遗憾相随的,是信中无所不在的紧迫感。越积越多的书,越买越多的唱片,越来越抖的手,越来越无力的双腿,越来越弱的视力,各种来不及完成的写作心愿……从第一封信到最后一封信,我看到父亲的衰老,无奈和不甘。他不怕死,真的不怕死,但是他怕愚蠢而无知地死去。他最大的心愿,就是要尽量做一个明白人。他知道自己的限度,但一直不放弃求知的努力。
在后期给李章的一封信中,他这样写道:
李章同志:
这个夏天,我才发现自己真是已经老了,而且老得厉害,这是前所未有的。症状是:走五百米以上,两腿就疲软,买米超过十二斤,拎起来就吃力得很,看书二十分钟,不休息一下就看不清楚了。尤其可怕的是早上爬起来,白天坐久了站起,头里便一阵黑,头昏眼花,不扶什么便站不稳。平时我经常不午睡,现在是终日老想睡,昏昏然。今年病倒过几次,虽过几天又起来,始终没能完全恢复过来。
这是自然法则,无法抗拒的。经过“史无前例”能幸存至今,又看了那么多好书,听到了那么多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音乐,这就该感谢上苍了。所以我并不颓丧,泰然处之,照旧读书不辍。只是家务多(特别是要照顾小孩),空闲太少,眼又坏了,看书很慢,买来的好书积压未看或未细看的不少,使人着急,有负债乃至负罪感。
熟悉父亲的人都知道,他这个人太好,但命运对他太不公,这辈子过得太苦,磨难冤屈之深重,没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难以想象。但是父亲说得也对,上苍另一方面待他也不薄,给了他音乐和书,还有李章这样的知音挚友,其道不孤,确是苦难人生中的难得的快乐。
还给了他觉悟:“早死晚死我不在乎,不死于浩劫,反而苟延残喘性命至今(81岁了!)真没想到。可庆幸者,‘若使当年身便死’,我就成了个糊涂鬼。一个愚蠢的拜神者。如今则不必为此自惭了。”
对一个劫后余生者,还有比这更好的安慰吗? ■
辛丰年致李章书信
《书信里的辛丰年》,辛丰年、李章著,“脉望丛书”系列之一,上海人民出版社8月即出。
本文作者严锋,文载2014年7月13日《东方早报·上海书评》。
|
|
 |联系我们|有害信息举报:010-60152166 邮箱:zx@jd-bbs.com|手机版|Archiver|黑名单|中国耳机爱好者俱乐部
( 京ICP备09075138号 )
|联系我们|有害信息举报:010-60152166 邮箱:zx@jd-bbs.com|手机版|Archiver|黑名单|中国耳机爱好者俱乐部
( 京ICP备09075138号 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