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
|
感谢关注耳机俱乐部网站,注册后有更多权限。
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,没有账号?注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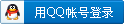
x
肖斯塔科维奇:一生都在等待枪决----原著 / 冷风过境
“等待枪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。”晚年的德米特里•肖斯塔科维奇向年轻的友人伏尔科夫讲述往事时,忽然沉默良久,然后如是说。伏尔科夫同情的看着这位苏联最负盛名的音乐家,那是一张满是孩子气的脸,圆圆的镜片,蓬松的头发,总是尴尬和手足无措的神情,谨慎得几乎称得上畏惧的眼睛,这张面孔是如此意味深长,一个时代对一颗灵魂所能造成的痛苦挤压,在这张脸上纤毫毕现。
当我们脏时爱我们
1934年,肖斯塔科维奇29岁,已经发表了一系列重要作品,是苏联音乐界最闪耀夺目的新星。这一年,他的歌剧《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》在列宁格勒举行首演,好评如潮,不久开始在欧美各国公演。一时间他集万千宠爱于一身,隐然已是苏联音乐第一人。
但这部红极一时的歌剧却惹恼了一个人,1936年,斯大林出席观看了该剧在莫斯科的首演,第一幕还没结束便愤然离场。1月28日,一篇题为《不是音乐是混乱》的文章出现在《真理报》上,对这部歌剧及其作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,所有人都知道这篇未署名文章的背后是谁,风向一下转变,各大报纸和乐评人纷纷对《真理报》利爪下的猎物口诛笔伐,各省的工人与农民聚集在广场上扬声抗议,转眼之间,肖斯塔科维奇变成了“人民的敌人”。
他是在外省巡回表演的路上读到这篇文章的,愤怒与耻辱令他透不了气,不久他更悲哀的发现,昨日还对他笑脸相迎,赞不绝口的朋友们突然一心要将他拉入地狱,愤怒中他对友人格里克曼说:“如果有一天,我的双手被砍断,我还可以用牙齿咬住笔继续谱写音乐。”
愤怒过后,恐惧如潮水般袭来。这一年苏联的大清洗进入高潮,2000多万知识分子被处决或莫名其妙地失踪,死神的镰刀在每个人的头顶挥舞。他意识到自己在劫难逃,像当时许多人一样,收拾起一只手提箱,静静的呆在家中,等着某个夜晚克格勃将他带走。他后来描述当时的心情:“我怀着一种有罪的感觉坐着,而事实上我没有犯任何罪。”
但他最终幸免于难,斯大林没有将他投入监狱,这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对他的统治是种有益的装饰。“斯大林喜欢把一个人与死神面对面地放到一起,然后让这个人按着自己的旋律跳舞。”他说。最终他选择了屈服,公开做了检讨。一年后,作为赎罪,他完成了《第五交响乐》,将它献给斯大林。这部作品为他赢回了一度失去的声誉,令他正式成为苏联音乐界第一人。
这场风波使他后半生都惴惴不安,他时常问别人:“如果你处于我的位置,你会怎样?”在他生前最后一部作品《列比亚德金上尉诗四首》中,主人公是一个可怜虫,被人像狗一样杀死,他为这个人配了充满柔情的音乐,他说:“当我们脏时爱我们,别在我们干净时爱我们。干净的时候人人都爱我们。”
做个渺小的提琴手
他本质上是一个蔑视强权的人,却不幸有着小人物般怯懦的性格。他无心成为极权之下的殉道士,于是便只有与当局保持表面的妥协与合作。和俄罗斯历史上许多呆在暴君身边的文艺家一样,他选择成为一个癫僧,这是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族群,类似于中国古代那些佯狂避世的智者,他们用疯癫的行为化解暴君的猜忌,偶尔甩出一两句尖刻锐利的话语,投进黑暗如水的专制体制之中。
在令人窒息的高压环境中,所有人都变得卑微而胆怯。他说:“那个时候,为了说个笑话,你就得把客人带到浴室里去。你得把水龙头开的大大的,然后把这个笑话低声告诉他。甚至笑也得轻轻地笑,用手捂住嘴笑。”他的两位好友兼保护人,苏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与先锋派导演梅耶荷尔德,都在大清洗中被处决了。梅耶荷尔德被逮捕时,后悔自己没有成为一个普通的小提琴手,而44岁的元帅在被捕前居然有着相同的心愿。“这种巧合使我感到惊讶和可怕。一位是名导演,一位是著名的将领——突然都希望做一个渺小的,不受注意的人,只想坐在乐队里拉拉小提琴。”
唯一高高在上的只有斯大林,他热衷干预一切文艺创作,而不是像太阳王路易十四那样,对艺术家们说:“这方面你们优先。”作为苏联音乐界第一人,他多次见过斯大林,“没见他有什么魔力。他是个貌不惊人的普通人,又矮又胖,头发略带红色,满脸的麻子,右手明显比左手瘦小,他总是藏着右手。他的相貌同无数画像上的样子一点也不像”。
他忘不掉30年代中期发生的一场悲剧,300多位乌克兰盲人歌手从各地汇集起来,参加官方组织的民间歌手大会,当这些“乌克兰活的博物馆,活的历史”聚齐之后,几乎全部被枪决了,他说,因为“这些可怜的盲人们,他们唱的是旧调子,但是乌克兰正在进行伟大的事业,而这些盲人,唱着暧昧的旧歌曲,他们的流浪的歌,审查员没有办法去审查。”于是就索性全部杀掉了。
他被斯大林命令与另一位音乐家哈恰图良合作,为新国歌谱曲。“这个主意愚蠢之至,哈恰图良和我风格不同,工作方法也不同……但是我们不得不服从。”一共有四首新曲参加了评选,评判专家们认为他与哈恰图良的最好,但副歌需要作少许修改。斯大林问他,需要用多少时间?他想说5分钟,但怕这样会被认为过于草率,于是改口说5个小时。结果斯大林还是皱起了眉头,最终他们的曲子落选了。哈恰图良事后责怪他,“假如你要求至少一个月的时间,也许我们就胜了……”
我的交响乐多数是墓碑
《第七交响乐》是他获得世界性声誉的一部作品。不管是对俄国人还是对美国人来说,二战时苏联的最高象征就是《列宁格勒交响乐》——德米特里•肖斯塔科维奇的《第七》。
1941年到1944年,是苏联抗击纳粹德国侵略的艰苦岁月。德军将列宁格勒团团围住,声言:“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投降,要将列宁格勒从地图上抹去。”在被围困的900天中,城内饥饿倒毙者仅官方统计就有60万人。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,肖斯塔科维奇在被围困的最初几个月里创作了这部作品。
1942年3月5日,他出逃到大后方古比雪夫市,和莫斯科大剧院乐团一起,在空袭警报中完成了《第七交响乐》的首演。5个月以后,乐谱被装入战斗机,飞行员冒着被击落的风险将它投入列宁格勒。此时饿殍满城的列宁格勒已经凑不齐一支完整的乐队,首次排练时只来了20个人,一半的乐手都是被担架抬来的,骨瘦如柴的指挥甚至挥不动指挥棒。仅经过一次15分钟的排练后,《第七交响乐》在列宁格勒大剧场首演了,饥饿的人们从四处聚拢进来,在德军的隆隆炮声中,乐团完美的完成了演出,许多乐手在结束的一刹那晕厥过去。
《第七交响曲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,它对苏联军民士气的提升是不可估量的。斯大林将它宣传为反法西斯的颂歌,并得到了盟国的好评。1942年7月19日,数百万美国人在电台里第一次听到了这首气势恢弘的音乐,《时代》杂志将作曲家身着消防制服、头戴消防帽的照片登上了封面——在他留守列宁格勒的日子里,他还是一个称职的民兵。
这也是他最富争议的一部作品,苏联官方宣扬这是一部反法西斯的杰作,他自己也曾如此附和,但在他死后发表的自传中,他推翻了这一说法:“《第七交响曲》是战前设计的,所以,完全不能视为在希特勒进攻下有感而发。侵犯的主题与希特勒的进攻无关。我在创作这个主题时,想到的是人类的另一些敌人。”“我毫不反对把《第七》称为《列宁格勒交响乐》,但它描写的不是被围困的列宁格勒,而是被斯大林所破坏、希特勒只是把它最后毁掉的列宁格勒。”
音乐艺术本身的多义性帮他隐藏了这个秘密,在他一生创作的15部交响乐中,多部作品都埋藏着巨大的悲痛,包括被公认是迎合斯大林的《第五交响乐》。官方对它的定义是充满欢欣与光明,但与他处境近似的作协主席法捷耶夫听出了异声,他在私人日记中写道:“《第五交响曲》的终曲是无可挽回的悲剧。”
他说:“我的交响乐多数是墓碑……我愿意为每个受害者写一首乐曲,但是这不可能,因此我把我的音乐献给他们全体。”
俄罗斯的良心
1948年, 政治再一次向他施压。2月,苏共中央对他作了严厉批评,他已写成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被认为含有“形式主义的危害”而未能公演,从此他中断交响乐写作达八年之久。他不得不抹去自我,弯曲着身子顺从权力,除了傀儡样地代表官方露面,就是写像“森林之歌”和“阳光照耀祖国”一类的音乐。
但他怯懦的外表下却不时迸发出锋利的光芒。他和马雅可夫斯基被西方看作是斯大林的两大御用文人,但他嘲笑这位苏联第一诗人:“在他的诗中,他蔑视巴黎和美国,但是他却喜欢去巴黎买衬衫,而且,如果爬到桌子底下去才能拣到一支美国钢笔的话,他也愿意爬的。”
终其一生,他都不愿与来苏联访问的左翼知识分子们交往,不管这人是萧伯纳还是罗曼•罗兰。他不信任这些西方人道主义者,尽管他们宣称喜爱他的音乐。他说:“这些人在苏联好吃好喝一顿,回国后就向世人描绘一个地上的人间天堂,他们真有那么愚蠢吗?”
他真正尊敬的是那些“俄罗斯的良心”。他欣赏斯特拉文斯基,赞美他的傲慢:“斯特拉文斯基对这些伪君子(苏联文化官员)中的一个人,没有伸出手让他去握,而是向他伸出了手杖,这个伪君子只得去握手杖,证明他才是真正的奴才。”演奏家尤金娜是他的朋友,有一天她收到了一个装有两万卢布的封袋,别人告诉她这是斯大林送来的,于是尤金娜给斯大林写了回信:“谢谢你的帮助,约瑟夫。我将日夜为你祈祷,求主原谅你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大罪。”她把这封自取灭亡的信寄了出去,万幸的是,斯大林在看完这封信后,还没来得及处置,几天后就死去了。
但他始终是斯大林粉饰太平的工具。1949年,他被派到纽约市,以苏联明星代表的身份出席世界和平文化与科学会议。在会场上,一个翻译为他代读发言稿,既攻击美国穷兵黩武,又对苏联的文艺成就大唱颂歌。然后,表演进入高潮部分,一个苏联官员当众问他:“你是否认为伊戈尔•斯特拉文斯基反动透顶?”他的嘴角和面颊开始抽搐,沉默片刻,他说:“是。”
13年后,“帝国主义的走狗”斯特拉文斯基回到阔别五十多年的苏联,立刻来看望他。两人四目相对,却无话可说。好一会儿,斯特拉文斯基打破了沉默:“我不喜欢普契尼。你呢?”“我也不。”他回答。这是谈话的开端,也是终结。就是最没想像力的人也不难揣测他那一刻的心情,那被人逼着向自己所敬佩的无辜者身上泼脏水的痛苦……
回头看,只有尸骨成山
晚年的他,喜欢向友人讲述果戈理的故事。1930年,人们在修建一座纪念碑时,掘开了旁边果戈理的墓,发现他不在棺材里。一具伟大的尸体跑掉了,人们谣传,这个年代太糟糕,连果戈理都受不了逃走了。政府开始调查原因,发现果戈理没跑多远,他就躺在附近,脑袋掉在一边。原来人们在竖起的纪念碑上放的砖头过多,砖头砸破了棺材,也砸掉了死者的脑袋。
这个死人从棺材出逃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他,晚年的他渐渐感到束缚在自己身上的网越收越紧。站在苏联音乐界荣耀的峰巅,他却禁不住害怕。作为一个时代的幸存者,他不怕死,但他担心死后的行状。他说:“一个人死了,别人就把他端上饭桌喂子孙后代。打个比方,就是把他收拾整齐送上亲爱的后代的饭桌,让他们胸前系着餐巾,手上拿起刀叉割死者的肉吃。你知道,死人有个毛病,就是凉得太慢,他们太烫,所以就给他们浇上纪念的汤汁——最好的胶质,把他们变成肉冻……”
在他生命的最后4年,他与年轻的音乐家伏尔科夫成为密友。在伏尔科夫的鼓励下,一个“从棺材里逃出去”的计划逐渐形成,他决定秘密口述一部回忆录,将真实的自己和真实的历史告诉大众,从而纠正那个“令人心碎的奴颜卑膝的形象”。他为伏尔科夫提供材料,讲述往事,肆意评价那些曾经的风云人物。在伏尔科夫完成写作后,他通读了全书,并逐章签名确认,同意在他死后将书稿送西方出版。
1975年9月,他死于肺癌,被葬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。如他所料,他被东西方阵营各取所需,大卸八块。苏联宣称他是“国家最忠实的儿子”,西方国家则称他为“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,苏维埃政权坚定的信徒。”一切仿佛盖棺论定,但他的幽灵却从强权与意识形态的铜墙铁壁中钻了出来,并顺手打了它们一记响亮的耳光——1976年,他的回忆录被伏尔科夫带到了国外,几年后,回忆录面世,题名《见证》。
这是他一生哀乐的见证,也是一个时代的见证,往事已然如烟,生灵早已涂炭,回首前尘,他的心中只剩一片怅然,就像他在生前向伏尔科夫讲述往事的时候,时常忍不住说的那样:“回头看,除了一片废墟,我什么也看不到,只有尸骨成山……”
[ 本帖最后由 bill1s 于 2010-4-25 16:55 编辑 ] |
|
 |联系我们|有害信息举报:010-60152166 邮箱:zx@jd-bbs.com|手机版|Archiver|黑名单|中国耳机爱好者俱乐部
( 京ICP备09075138号 )
|联系我们|有害信息举报:010-60152166 邮箱:zx@jd-bbs.com|手机版|Archiver|黑名单|中国耳机爱好者俱乐部
( 京ICP备09075138号 )